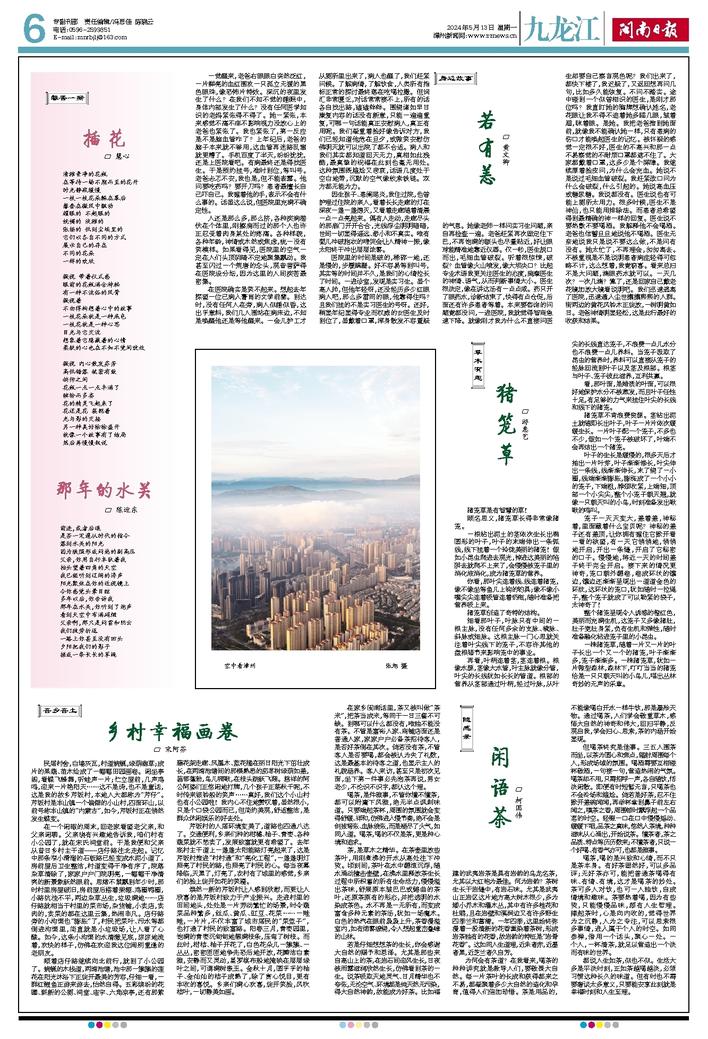▱ 黄文卿
一觉醒来,老爸右眼眼白突然泛红,一片鲜亮的血红围攻一只孤立无援的黑色眼珠,像恐怖片特效。深沉的夜里发生了什么?在我们不知不觉的睡眠中,身体内部发生了什么?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老妈紧张得不得了。她一紧张,本来感觉不痛不痒不影响视力没放心上的老爸也紧张了。我也紧张了,第一反应是不是脑血管咋了?上年纪后,老爸的脑子本来就不够用,这血管再迷路乱窜就更糟了。手机百度了半天,纷纷扰扰,还是上医院看吧。有病最终还是得找医生。于是预约挂号,准时到位,等叫号。老爸忐忑不安,我也是,但不能表露。他问要吃药吗?要开刀吗?患者最擅长自己吓自己。我握着他的手,表示不会有什么事的。话虽这么说,但医院里充满不确定性。
人还是那么多,那么挤,各种疾病潜伏在个体里,刚擦肩而过的那个人也许正忍受着肉身某处的疼痛。各种样貌,各种年龄,神情或木然或焦虑,统一没有笑模样。如果看得见,医院里的空气一定在人们头顶阴晴不定地聚集飘动。我甚至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,观音菩萨得在医院设分坛,因为这里的人间疾苦最密集。
在医院确实是笑不起来。想起去年探望一位已病入膏肓的文学前辈。到达时,没有任何人在旁,病人似睡似昏,这出乎意料,我们几人围站在病床边,不知是唤醒他还是等他醒来。一会儿护工才从厕所里出来了,病人也醒了,我们赶紧问候。了解病情,了解饮食,人类所有指标正常的探讨最终落在吃喝拉撒。但词汇非常匮乏,对话常常接不上,所有的话各自找出路,磕磕绊绊。围绕诸如早日康复内容的话没有新意,只能一遍遍重复,可哪一句话能真正安慰病人,真正有用呢。我们凝重着脸好像告诉对方,我们已经知道他危在旦夕,或微笑安慰仿佛明天就可以出院了都不合适。病人和我们其实都知道回天无力,真相如此残酷,最真挚的祝福在此刻也毫无用处。这种氛围既尴尬又悲哀,话语几度处于空白地带,沉默的空气像绞索铁链。双方都无能为力。
因生孩子、患阑尾炎,我住过院,也曾护理过住院的亲人,看着长长走廊的灯在深夜一盏一盏熄灭,又看着走廊随着清晨一点一点亮起来。偶有人走动,走廊尽头的那扇门开开合合,光线浮尘明明暗暗,世间一切显得遥远、渺小和不真实。唯有婴儿冲破胞衣的啼哭会让人精神一振,像太阳终于冲出层层浓雾。
医院里的时间是破的,稀碎一地,还是慢的,步履蹒跚。好不容易等到叫号,其实等的时间并不久,是我们的心情拉长了时间。一进诊室,发现是实习生。虽个高人帅,但他年轻呀,还没经历多少红眼病人吧,那么多雷同的眼,他靠得住吗?且我们挂的不是实习医生的号呀。还好,稍显年纪显得专业而权威的女医生及时到位了,虽戴着口罩,浑身散发不容置疑的气息。她像老师一样问实习生问题,亲自再检查一遍。老爸赶紧再次固定住下巴,不再饱满的额头也尽量贴近,好让眼球能精准地靠近仪器。仅一秒,医生脱口而出,毛细血管破裂。听着很惊悚,破裂?血管像火山喷发,像大坝决口?比起专业术语我更关注医生的态度,揣摩医生的神情、语气,从而判断事情大小。医生很淡定,像在讲这汤有一点点咸。药只开了眼药水,诊断结束了,快得有点仓促,后面还有许多患者等着。本来要咨询的问题竟都没问,一进医院,我就觉得智商急速下降。就像刚才我为什么不直接问医生却要自己察言观色呢?我们出来了,都快下楼了,我迟疑了,又返回想再问几句,比如多久能恢复。不问不踏实。途中碰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医生,是刚才那位吗?我直盯她的胸牌想确认姓名,老花眼让我不得不追着她多瞄几眼,皱着眉,眯着眼。是她。我把老爸推到她面前,就像我不能确认她一样,只有患病的伤口才能唤起医生的记忆。被怀疑的感觉一定很不好,医生的不高兴和那一点不易察觉的不耐烦口罩都遮不住了。大家都戴着口罩,这多少是个屏障。我继续厚着脸皮问,为什么会充血。她说不是说过毛细血管破裂。我赶紧改口问为什么会破裂,什么引起的。她说高血压或糖尿糖。我说都没有。医生说也有可能上厕所太用力。很多时候,医生不是神仙,也只能用排除法。而患者总希望得到最精确的神一样的回复。医生说不要热敷不要喝酒。我解释他不会喝酒。老爸也信誓旦旦地说他不喝酒。医生无奈地说我只是说不要这么做,不是问有没有。她太忙了,不再理会,匆匆离去。不被重视是不是说明患者病症轻得可忽略不计,这么想着,我竟窃喜。看来总归不是大问题,滴眼药水就可以。一天几次?一次几滴?算了,还是回家自己戴老花镜加放大镜看说明吧。我们迅速逃离了医院,迅速遁入尘世攘攘熙熙的人群。街两边的黄花风铃木正绽放,一树明黄如日。老爸神情明显轻松,这是此行最好的收获和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