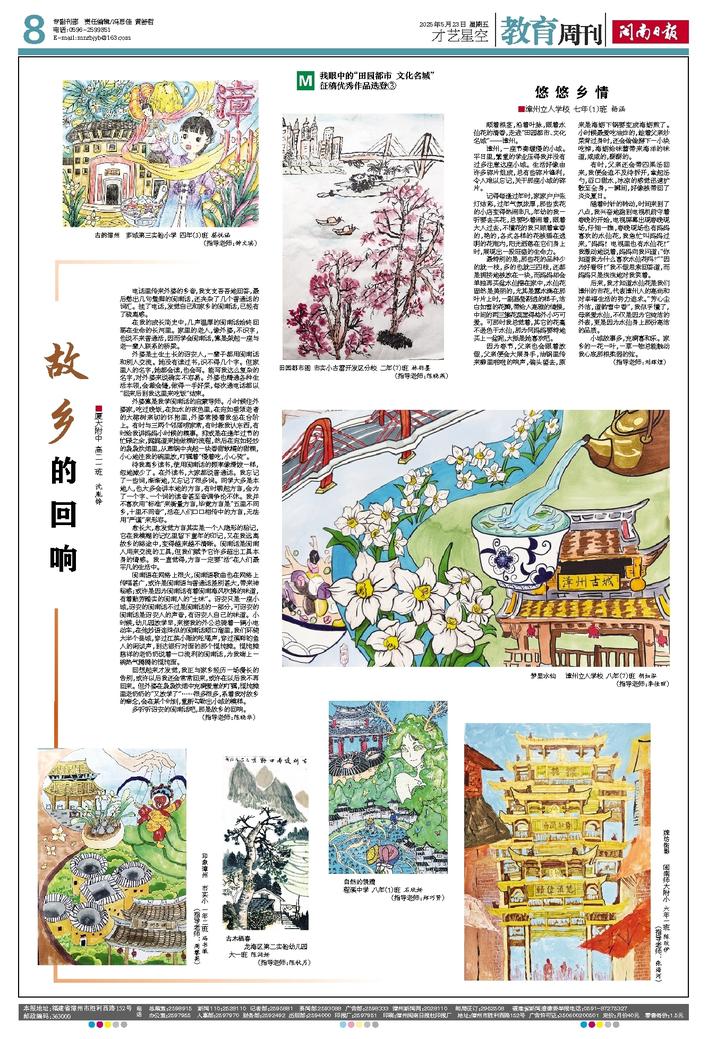■厦大附中 高二一班 沈胤铮
电话里传来外婆的乡音,我支支吾吾地回答,最后憋出几句蹩脚的闽南话,还夹杂了几个普通话的词汇。挂了电话,发觉自己和家乡的闽南话,已经有了疏离感。
在我的成长简史中,几声温厚的闽南话始终回荡在生命的长河里。家里的老人,像外婆,不识字,也说不来普通活,因而学会闽南话,算是架起一座与老一辈人联系的桥梁。
外婆是土生土长的诏安人,一辈子都用闽南话和别人交流。她没有读过书,识不得几个字。但家里人的名字,她都会读,也会写。能写我这么复杂的名字,对外婆来说确实不容易。外婆也精通各种生活本领,会裁会缝,做得一手好菜,每次通电话都以“回来后到我这里来吃饭”结束。
外婆算是我学闽南话的启蒙导师。小时候住外婆家,吃过晚饭,在如水的夜色里,在宛如垂须老者的大榕树亲切的怀抱里,外婆常搂着我坐在台阶上。有时与三两个邻居唠家常,有时教我认东西,有时给我讲妈妈小时候的糗事。抑或是在逢年过节的忙碌之余,娓娓道来她做粿的流程,然后在宛如轻纱的袅袅炊烟里,从蒸锅中夹起一块香甜软糯的甜粿,小心地往我的碗里放,叮嘱着“慢着吃,小心烫”。
待我离乡读书,使用闽南话的频率像滑坡一样,忽地减少了。在外读书,大家都说普通话。我忘记了一些词,渐渐地,又忘记了很多词。同学大多是本地人,也大多会讲本地的方言,有时聊起方言,会为了一个字、一个词的读音甚至音调争论不休。我并不喜欢用“标准”来衡量方言,毕竟方言是“五里不同乡,十里不同音”,活在人们口口相传中的方言,无法用“严谨”来形容。
愈长大,愈发觉方言其实是一个人隐形的胎记,它在我模糊的记忆里留下童年的印记,又在我远离故乡的路途中,变得越来越不清晰。闽南话是闽南人用来交流的工具,但我们赋予它许多超出工具本身的情感。我一直觉得,方言一定要“活”在人们最平凡的生活中。
闽南语在网络上很火,闽南语歌曲也在网络上传唱甚广,或许是闽南语与普通话差别甚大,带来神秘感;或许是因为闽南话有着闽南海风吹拂的味道,有着勤劳踏实的闽南人的“土味”。诏安只是一座小城,诏安的闽南话不过是闽南话的一部分,可诏安的闽南话是诏安人的声音,有诏安人自己的味道。小时候,幼儿园放学早,来接我的外公总骑着一辆小电动车,在他妙语连珠似的闽南话顺口溜里,我们环绕大半个县城,穿过江滨小贩的吆喝声,穿过溪畔钓鱼人的闲谈声,到达银行对面的那个馄饨摊。馄饨摊慈祥的老奶奶说着一口流利的闽南话,为我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面。
回想起来才发觉,我正与家乡经历一场漫长的告别,或许以后我还会常常回来,或许在以后我不再回来。但外婆在袅袅炊烟中充满爱意的叮嘱,馄饨摊里老奶奶的“又放学了”……很多很多,系着我对故乡的牵念,会在某个时刻,重新勾勒出小城的模样。
多听听诏安的闽南话吧,那是故乡的回响。
(指导老师:陈晓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