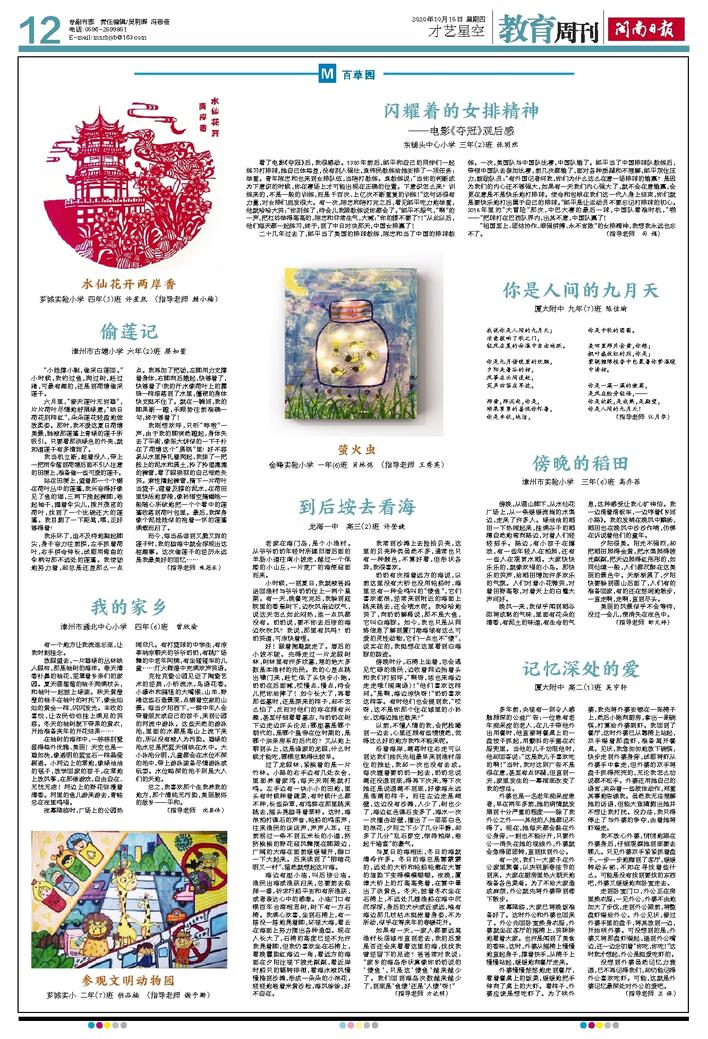老家在海门岛,是个小渔村。从爷爷奶奶年轻时所建旧厝后面的羊肠小道往南小坡走,越过一个低矮的小山丘,一片宽广的海便迎面而来。
小时候,一到夏日,我就被爸妈送回渔村与爷爷奶奶住上一两个星期。有一天,晚餐吃完后,我躲到庭院里的香蕉树下,边吹风扇边叹气,说这天怎么如此闷热,连一点风都没有。奶奶说,要不你去后垵的海边吹吹风?我说,那里有风吗?奶奶笑道,可凉快着哩。
好!趿着拖鞋就走了。厝后的小坡不陡。先得走过一片龙眼树林,树林里有许多坟墓,埋的绝大多数是本渔村的先民。我的心差点跳出嗓门来,赶忙低了头快步小跑。奶奶在后面喊,哎慢点、慢点,待会儿把你给摔了!如今长大了,再看那些墓时,还是原来的样子,却不怎么怕了,反而对他们的存在颇有兴趣,甚至仔细看看墓志,与奶奶在树下边走边评头论足:哪座墓是哪个朝代的,是哪个皇帝在位时期的,是哪个宗亲房系的后代的?又从地上聊到头上,这是谁家的龙眼,什么时候才能吃,哪棵总熟得比较早。
过了龙眼林,紧挨着的是一片竹林。小路的右手边有几处农舍,里面养着家鸡,每天天刚亮就打鸣。左手边有一块小小的田地,里头有时候种着蔬菜,有时候什么都不种,长些杂草,有鸡群在那里跳来跳去,摇头晃脑寻着草籽。这时,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,轮船的鸣笛声,往来渔民的谈话声,声声入耳。往前拐过一条不到五米长的小道,挤挤挨挨的野花迎风舞摆在脚跟边,广阔的大海在面前缓缓铺开,胸口一下大起来。后来读到了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,猛然就想起这片海。
海边有座小庙,叫后垵公庙。渔民出海或渔获归来,总要前去祭拜一番,祈求行船平安和有所渔获,或者表达心中的感激。小庙门口有棵百年台湾相思树,树下有一方石椅。我满心欢喜,坐到石椅上,有一搭没一搭地晃着脚,环视大海,看云在海面上努力摆出各种造型。现在人长大了,石椅的高度已经不允许我晃着脚,但我仍喜欢坐在石椅上,看晚霞染红海边一角,看远方的海面在夕阳注视下波光粼粼,看近岸时船只的辗转徘徊,看海水被风慢慢推到沙滩,形成一朵朵的小浪花,轻轻地卷着米黄沙粒,海风徐徐,好不自在。
我常到沙滩上去捡拾贝壳,这里的贝壳种类虽然不多,通常也只有一种颜色,不算好看,但形状各异,我很喜欢。
奶奶有次指着远方的海说,以前这里没有大桥也没用轮船时,海里总有一种会鸣叫的“傻鱼”,它们喜欢逐浪,经常来到附近的海面上跳来跳去,还会喷水呢。我哈哈地笑了,向奶奶解释说,那不是大鱼,它叫白海豚。如今,我也只是从网络信息了解到厦门港海域有这么可爱的灵性动物,它们一点也不“傻”,说实在的,我挺想在这里看到白海豚的踪迹。
傍晚时分,石椅上坐着,总会遇见忙碌的渔民,边收着网边抬着头和我们打招呼。“啊呀,恁也来海边走走哦(闽南语)!”他们喜欢这样问。“是啊,海边凉快呀!”奶奶喜欢这样答。有时他们也会提到我,“哎呀,这不是你那个住在城里的小孙女,这海边她也敢来?”
以前,不懂人情的我,会把脸撇到一边去,心里还颇有些愤愤然,觉得这么好的地方我咋不能来呢。
沿着海岸,潮落时往右走可以到达我们姓氏先祖最早来到渔村居住的残址,我却一次也没有去成。每次缠着要奶奶一起去,奶奶总说潮还没退到底,得再下次来,等下次她还是说退潮不到底,好像海永远是涨潮的样子。而往左边走是峭壁,这边没有沙滩,人少了,树也少了,海边红色礁石变多了,海水一次一次撞击岩壁,撞出了一层层白色的浪花,夕阳之下少了几分平静,却多了几分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的豪气。
与夏日的海相比,冬日的海就清冷许多。冬日的海总是雾蒙蒙的,远处的大桥和轮船轮廓在大雾的渲染下变得模模糊糊。夜晚,厦漳大桥上的灯高高亮着,在雾中晕出了淡黄色。冬天,披着冬衣坐在石椅上,不远处几艘渔船在海中沉沉浮浮,身后的犬吠或近或远,唯有海边那几枝枯木挺拔着身姿,不为所动,似乎在等来年的春暖花开。
如果有一天,一家人都要远离渔村长居城市直到老去,我的后辈是否还会来看看这里的海,找找我曾经留下的足迹?爸爸常对我说:“家乡的海岛形状真像你奶奶说的‘傻鱼’,只是这‘傻鱼’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回到海岛次数越来越少了,到底是‘鱼傻’还是‘人傻’呀!”
(指导老师 方达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