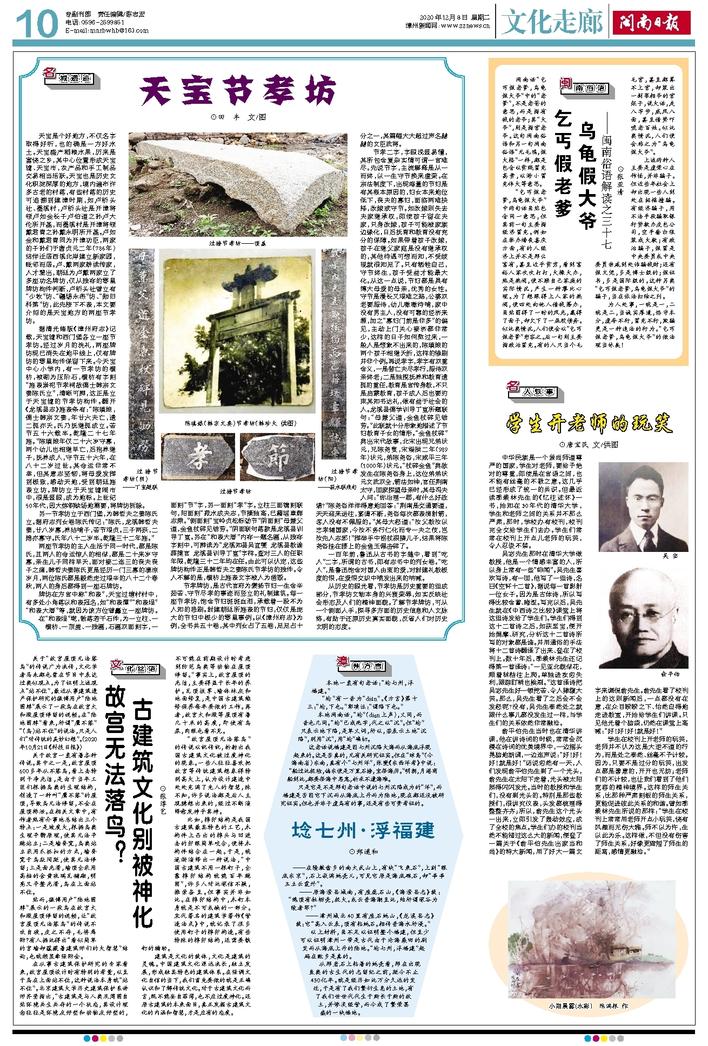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师道尊严的国家,学生对老师,要给予绝对的尊重,即使是在言语之间,也不能有丝毫的不敬之意。这几乎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共识。但最近读季羡林先生的《忆往述怀》一书,始知在30年代的清华大学,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严肃,那时,学校办有校刊,校刊完全交给学生们去办。学生们常常在校刊上开点儿老师的玩笑,令人忍俊不禁。
吴宓先生那时在清华大学做教授,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,所以身上常有一些“绯闻”。吴先生喜欢写诗,有一回,他写了一组诗,名曰《空轩十二首》,据说每一首影射一位女子。因为是古体诗,所以写得比较含蓄、晦涩。写完以后,吴先生就在《中西诗之比较》课堂上将这组诗发给了学生们。学生们得到这十二首诗之后,如获至宝,便开始揣摩、研究,分析这十二首诗所写的对象都是谁。并用通俗的手法将十二首诗翻译了出来、登在了校刊上。数十年后,季羡林先生还记得第一首译诗:“一见亚北貌似花,顺着秫秸往上爬。单独进攻忽失利,跟踪盯梢也挨刷。”这首译诗把吴宓先生好一顿挖苦、令人捧腹大笑。那么,吴先生看了之后会不会发怒呢?没有,吴先生泰然处之就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,与学生们的关系依然非常融洽。
俞平伯先生当时也在清华讲课,他在讲诗词的时候,常常会沉浸在诗词的优美境界中,一边摇头晃脑地朗诵,一边连声说:“好!好!好!就是好!”话说忽然有一天,人们发现俞平伯先生剃了一个光头,俞先生在太阳下走着,光头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。当时的教授和学生们,没有剃光头的。特别是那些教授们,很讲究仪表,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;所以,俞先生这个光头一出来,立即引发了轰动效应,成了全校的焦点。学生们办的校刊当然不能错过这么大的新闻,便登了一篇关于《俞平伯先生出家当和尚》的特大新闻,用了好大一篇文字来调侃俞先生。俞先生看了校刊上的这则新闻后,一点都没有在意,在众目睽睽之下、怡然自得地走进教室,开始给学生们讲课。只见他光着个脑袋,仍然在课堂上高喊:“好!好!好!就是好!”
学生在校刊上开老师的玩笑,老师并不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,而是处之泰然、丝毫不予计较。因为,只要不是过分的玩笑,出发点都是善意的,开开也无妨;老师们的不计较,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宽容的精神境界。这样的师生关系,比那种严肃刻板的师生关系,更能促进彼此关系的和谐。曾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:“学生在校刊上常常用老师开点小玩笑,饶有风趣而无伤大雅。师不以为忤,生以此为乐。这样做,不但没有伤害了师生关系,好像更缩短了师生的距离,感情更融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