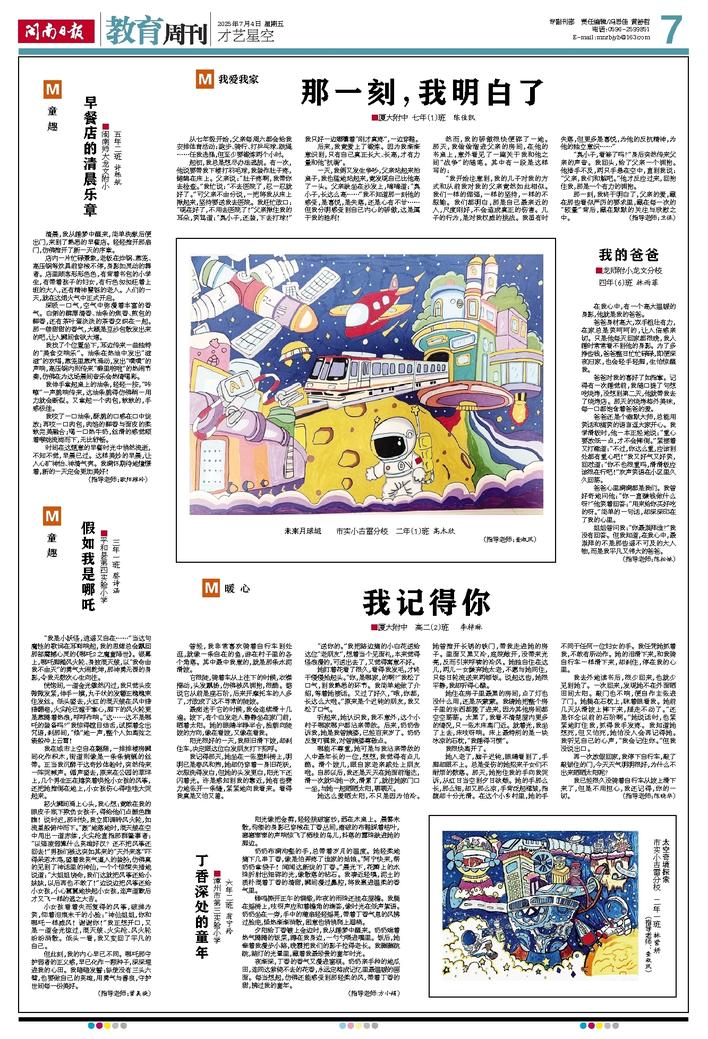曾经,我非常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逛,就像一条自在的鱼,游在村子里的各个角落。其中最中我意的,就是那条水泥滑坡。
它很陡,骑着车从上往下的时候,衣襟摆动,头发飘扬,仿佛被风拥抱,很酷。据说它从前是座石阶,后来开摩托车的人多了,才改成了这不寻常的陡坡。
最痴迷于它的时候,我会连续滑十几遍。坡下,有个白发老人静静坐在家门前,晒着太阳。她的眼睛半睁半合,脸朝向陡坡的方向,像在看坡,又像在看我。
阳光很好的一天,我照旧滑下坡,却刹住车,决定跟这位白发朋友打下招呼。
我记得那天,她坐在一张塑料椅上,明明已是春风和煦,她却仍穿着一身旧花袄,衣服洗得发白,但她的头发更白,阳光下还闪着光。许是感知到我的靠近,她有些费力地张开一条缝,紧紧地向我看来。看得我真是又怕又羞。
“送你的。”我把路边摘的小白花送给这位“老朋友”,想着当个见面礼,本来觉得怪浪漫的,可送出去了,又觉得寓意不好。
她盯着花看了很久,看得我发毛,才终于慢慢抬起头。“你,是哪家,的啊?”我松了口气,到我熟悉的环节。我简单地做了介绍,等着她接话。又过了好久,“哦,你都,长这么大啦。”原来是个迟钝的朋友,我又松了口气。
听起来,她认识我,我不意外,这个小村子哪家哪户都沾亲带故。后来,奶奶告诉我,她是我曾姨婆,已经百来岁了。奶奶反复叮嘱我,对曾姨婆尊敬点。
哪能不尊重,她可是与我沾亲带故的人中最年长的一位,想想,我觉得有点儿酷。滑个坡儿,跟自家老亲戚处上朋友啦。自那以后,我还是天天在她面前溜达,滑一次就叫她一次,滑累了,就往她家门口一坐,与她一起晒晒太阳,聊聊天。
她这么爱晒太阳,不只是因为怕冷。她曾推开长锈的铁门,带我走进她的房子。里面又黑又冷,庭院敞开,没带来光亮,反而引来呼啸的冷风。她独自住在这儿,两儿一女嫌弃她太老,不愿与她同住,只每日轮流送来两顿饭。说起这些,她很平静,我却听得心酸。
她住在房子里最黑的房间,点了灯也没什么用,还是灰蒙蒙。我猜她把整个房子里的东西都搬了进来,因为其他房间都空空荡荡。太黑了,我看不清楚屋内更多的情况,只一张木床离门近。就着光,我坐了上去,床吱呀响。床上最特别的是一块冰凉的石枕,“我睡得习惯”。
我很快离开了。
她人老了,脑子迟钝,眼睛看到了,手脚却跟不上。总是受伤的她招来子女们不耐烦的数落。那天,她抱住我的手向我哭诉,从红日当空到夕日欲颓。她的手那么长,那么细,却又那么凉,手背泛起褶皱,指腹却十分光滑。在这个小乡村里,她的手不同于任何一位妇女的手。我任凭她抓着我,不敢有所动作。她的泪滑下来,和我骑自行车一样滑下来,却刹住,停在我的心里。
我去外地读书后,很少回来,也就少见到她了。一次回来,发现她不在外面晒田间太阳。敲门也不响,便自作主张进了门。她躺在石枕上,眯着眼看我。她前几天从滑坡上摔下来,腿走不动了。“还是怀念以前的石阶啊。”她说话时,也紧紧地盯住我,抓得我手发疼。我知道她想死,但又怕死,她怕没人会再记得她。我听见自己的心声,“我会记住你。”但我没说出口。
再一次放假回家,我停下自行车,敲了敲锁住的门,今天天气明明很好,为什么不出来晒晒太阳呢?
我已经很久没骑着自行车从坡上滑下来了,但是不用担心,我还记得,你的一切。(指导老师:陈晓华)